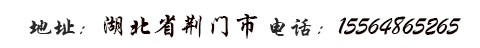李红卡少年2沈丘专栏
|
作 伴 结 庐 香 落 尘 外 专栏主编:鹿斌 专栏副主编:刘彩珍张杰民王倩倩 文:李红卡 图:堆糖 4。 村子里放上了电影,人们很喜欢这件事的。一整个下午很多人就议论了起来。孩子们更是着急,嚷嚷着要看电影。大人们不住地劝着,说是到了晚上才行的。于是孩子们就开始盼望天黑。天终于黑了下来。而且老远就能听得见嘈杂的人声,还有非常响亮的大喇叭的声响。那里不知道在传着什么话语,好像是宣布电影马上就要开始。道路上的行人不断,他们走着、说着,叫喊着。手电筒的强烈光线在行人中穿过,照在了人的一张脸上,于是那人就像瞎了似的乱撞起来。整条道路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笑声,一直延伸至那最热闹的电影场地。 少年也像其他的孩子一样草草地吃了一点晚饭,急不可耐地就要跑去。妈妈阻拦说:“早着哩!吃饱了再去。”少年不觉得自己饿,他只是怕耽误了那精彩的场面。来到了电影场地,眼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可真多啊!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也有用板车拉着小孩儿的,甚至稍远一点的墙垛上也坐满了人。闲谈着的,磕着瓜子的,抽着烟的等等都在等待着电影的开始。人群中央一杆竹竿上挂着一盏极亮的电灯,照得人的眼睛像是睁不开似的。那下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放映机。圆圆的影片盘已经架在了上面。对面不远处的一张很大的白色银幕牢牢地拴在两棵树之间。借着电灯的光线,能够看得清一个方形的大广播也绑在了其中的一棵树上。放映机周围人头攒动,一张张惊喜的面孔,一双双瞪得很大的眼睛,一起朝向那块白色的银幕,也一起集中在那即将转动的影片盘上。 随着广播中的一声宣布,“电影开始……”电灯灭了下来,一道彩色的光束直射向银幕,此时人们也仿佛安静了许多,都很专注地望着那些活动着的精彩画面。一盘结束之后,电灯亮了起来,很快的,又是下一盘。灯灭之后,银幕上继续展现着那些夺人耳目的画面,也继续上演着一段段的动人故事。握拳推掌、舞枪弄棒、飞檐走壁、挥刀耍剑等这些内容令高昂着脸的看客们深深地入了迷。他们有的模仿影片中的人物的语言,有的模仿人物的动作,也有的青年男女躲在人群的背后模仿演绎着浪漫的青春故事。 一个晚上能放映两部影片,三部、四部的也有,但却极少。谁家孩子考大学,谁家儿子结婚办喜事,谁家添丁增娃,总之只要有这样的喜事出现就要放电影的。有时村委会也要利用放电影的机会向村民宣布消息。一般是在放映的中途,村委会干部拿着盒装的话筒开始讲话,很多村民们边抽烟,边议论着,会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儿。 一场电影的结束,时间已经很晚,很多小孩子早已睡着在大人的怀中或者板车之上。夜色很浓,不远处传来狗的叫声。人们纷纷离场,此时电影场地仿佛一下子开阔起来,灯光也散布得很远。少年急忙回到自己的家去。不知妈妈是否已经睡熟。轻轻敲敲房门,妈妈开始说话:“是恒吗?”少年说:“是。”妈妈打开屋门,少年进入自己的屋子内,迅速地爬上床,开始睡下,而此时那些活动的画面,生动的故事仿佛还在他的脑海中,伴着即将入眠的他慢慢地开始模糊起来。妈妈再一次睡下,其实妈妈也是喜欢看电影的,但必须是戏曲片妈妈才看,比如什么“寇准背靴”“抬花轿”“花打朝”之类。在妈妈的眼中,戏曲片很花,很好看;在妈妈的耳朵中,戏曲片好听。而爸爸则有些不同,少年就像他的爸爸一样爱看电影。然而戏曲片放映的机会很少,大多是些武打、枪击、反间谍也或者其他的故事片。但无论哪一种影片总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令人快活,给单调生活着的乡间村民带来无穷的乐趣。 头天晚上看了电影,到了第二天的一大早,孩子们来到了学校。此时真是表现孩子们口才和表演技能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男孩子,他们大声议论着,热烈地比划着影片中的某个人物的武功如何高超,某个好人的愿望如何实现,某个坏人终得恶果等等。无论是那些打斗的场面,还是那些激烈的对白,在这些孩子们的口中,脑海中,就像是一次电影的回放。直到老师的出现,这些孩子才弯腰缩脖似的各回各位,教室内开始响起了嘹亮的读书声。 在学校的东侧是一片很宽广的空地,挨着路边有几棵高大的桐树,这样的场地很适合放映电影。的确,在这里也是经常能在晚上看到电影的。少年每天早晨从此经过,他能及早地见到有些老爷爷左臂挂着箩子筐,右手扛着铁锨在路边铲牛粪或者羊粪。起的早一些他们能铲半个箩子筐的好肥料。也有的老爷爷在昨晚的电影场地上弯腰捡拾些烟头,拨出里边的烟叶,好自己重新卷烟吸。少年也会来这里看一看的,少年对这里的地面上的碎影片特别感兴趣。电影在放映的过程当中,或者他们在整理影片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断掉的如大拇指或者指甲盖一般大小的片子。少年仔细发现,能够捡拾一些这样的东西。少年把片子举起来,借助亮光看得清楚。有时也会在家里把这些一小截儿一小截儿的片子贴在手电筒灯头的玻璃片上,开灯之后,在雪白的墙壁上显示出一些画面来。这些指甲盖般大小的碎影片成了少年生活中的一种令他特别喜欢的玩具。他会带上他的弟弟一起玩儿,一起借助一些光线,并告诉他的弟弟,这是在放电影。很多时候,少年会在纸面上把这样的场景画下来。画上放映机,画上银幕,在他所画的银幕上也画上一些人物等。不仅如此,他也要模拟一些声音,说出一些对白似的话语,这也许是少年在自我创造快乐,自我陶醉在他的故事中。 一天上午快放学的时候,老师突然宣布一个消息,说是让大家下午看电影。孩子们都知道晚上看电影,下午怎么看?大家是既惊奇又兴奋。教室内像是炸开了锅一般。老师反复拍着手掌示意大家静下来。老师又很神秘似的说,看电影时有手绢的就带上手绢儿。这一点更是令孩子们吃惊。老师没告诉孩子们为什么这样做。老师只说是带着大家一起到不远处的一个村子里。那里有一个厂房,很大的,放映的是对孩子们很有教育意义的片子,很值得看的。同学们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期待着下午的到来。少年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及早地吃过午饭,很快地就来到了学校。少年没有手绢儿,这东西只有女生有,男生哪会有手绢呢?往往有些男生哭鼻子、淌眼泪的,也只是用自己的衣袖顺势一擦,所以学校里的有些男生的衣袖、衣襟前总是黑乎乎的一片。大人们常常打趣说,都能擦着火柴了。但其实这也只是那些低年级的孩子才有的事情,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很讲卫生,穿着也干净。 孩子们紧跟着老师来到了那个叫赵庄的地方。这里果然有一处厂房,里边黑乎乎的看不到对面孩子的脸。大家几乎是凭着脚底的感觉慢慢地走到里边的,挨着坐了下来。不多时电影开演,影片的名字叫“妈妈再爱我一次”。故事讲的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寻找失踪18年的母亲的故事。这位医生很小的时候在学校里学会了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18年后,他终于找到了他心爱的妈妈,便用这首“世上只有妈妈好”重新唤醒母亲尘封多年的记忆,母子相认团圆。看完影片之后,同学们早已哭的稀里哗啦。这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老师要让他们带上手绢。也就是从那时起,同学们才知道“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而且大家都能够把这首歌唱下来。 冬天来了,下雪的季节也来了。孩子们很是喜欢玩雪,他们甚至把雪团成雪球儿放在口中品尝起来,那种凉滋滋的感觉令孩子们很爽快。一根冰条儿,一块冰片都成了他们的好玩具,但这些东西很快的融化成水。天气最冷的时候,水面上的冰很厚。胆大的孩子会站在上面,一直走到对岸,胆小的孩子也只是慢慢的站在边儿上,或者用一些小石子、小瓦片之类的东西贴水面甩去,啾啾啾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很快的,就要过年了,大人小孩儿都非常喜欢过年,尤其是孩子们,他们认为过年既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同时也能穿上新衣服,所以对孩子们来说,过年是他们特别盼望的一件大事。他们想,说不定春节过后还能得到几毛钱的压岁钱呢!村上也更是热闹,路上行人不断,买棵甘蔗,称些瓜子、花生的人很多。而在春节前后的这么多天里,少年家的店面里生意很好。他的爸爸进足各种货物,同时也进一批年画。不仅把年画挂得屋子满满,而且外墙壁上也挂了很多。为了方便路人,爸爸也把部分常用的货物搬到了路边,放在了一张板床之上,一家人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少年也总是守在摊子旁,看着那些挑挑拣拣的顾客。 有人传出消息说,学校里要放电影了。学校怎么会放电影呢?原来是有人借助学校的教室场地放电影,但那是要卖票收费的。放假之后,同学们离开了学校,自然学校空了下来。学校的确是个很好的场地。也就是在春节过后的几天里,学校里并不安静,大喇叭里传出了很多的音乐,也有很多的剧中的声音。那些安排组织放电影人仿佛很讲究似的,在学校外墙的黑板上写上“电影预告”。每天放映的电影的名称都在上面,什么“神龙剑侠吕四娘”,什么“长城大决战”等等,光看这些名字就足以令人们心动,但是少年看不了这个,因为一张票价是五角钱,他的爸爸是不会给他的。少年每天听着喇叭中传出的音乐和那些剧中的声音,他想象着那些生动的故事。有一些人物,他们的形象,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动作仿佛很清晰似的。渐渐地,少年感觉到每天放出了声音几乎是一样的,听的次数多了,他都能唱出那些歌曲,或者说出那些对白。 春节过后的第八天,学校里就要开学了。同学们开始来到了学校,这时电影也就结束了。教室外墙壁的黑板上“电影预告”还依然清晰,孩子们对此指指点点。少年也来到了学校里,但这一次是他的爸爸领着他来的,因为刚开学既要交书费,又要交学费。不仅是他的学杂费,还有他的弟弟的学杂费,那是他的爸爸卖掉很多货物才积攒下来的几十块钱。爸爸见着学校的会计,把两个孩子的书费、学费都交给了他。爸爸收下两张条子,装在了自己的口袋中。 屋子里站满了好多的人,他们大概都是办同样的事情。 5。 交了学杂费之后,少年已经进入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过完暑假之后,他就要进入四年级了。 春节刚过不久,路上的行人依然不断。他们走亲访友,有的挎着竹篮步行着,有的骑着自行车,竹篮绑在了车子的后座上,里边放着果品,馒头等。上面盖着一条大红的毛巾。渐渐地,就到了正月十五的这一天,集市上卖烟花,卖灯笼的人多起来。还有的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好多自扎的纸灯笼,为了不错过最好的出售时机,快速地往集市赶去。那些各色的烟花和灯笼也是孩子们的最爱。大人们也是为了哄孩子开心,买些小烟花,比如“小蝴蝶”,“小火鞭”之类的让孩子们玩玩。灯笼,自然是要买的。孩子们挑着花灯满村走动。有些好事的大人往往会让孩子们一起比赛碰灯。最终,有的纸灯笼会在一团火光中烧得只剩下一只小蜡烛和一根竹竿。为这样的事,孩子们是不会哭闹的,因为大人们会为他们再买一盏新的灯笼。到了十五的晚上,天空中灿烂的烟花多了起来。随着一声声如雷鸣般的声音响起,天空中一团一团的火花四散开来,把整个夜空都照得明亮。孩子们在忽闪忽闪的火光中甩起了火鞭,举着火花条儿,他们跑着、叫着、也欢笑着。 过完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年味儿才渐渐地淡下来,农人们有的忙着家里,有的忙于田间,反正是各做各的事去。 少年每天放学回家也学会了为妈妈帮忙干活。妈妈做饭,在灶台边忙着。少年就蹲在灶火口前生火。灶内的火苗子蹿了出来,少年就少放些柴。锅中白色的烟雾升腾,弥漫在整个厨房内。妈妈在烟雾中做着面食,锅内的热水上下翻滚,并发出咕嘟咕嘟的叫声。饭做熟了,少年的饭量很小,一小碗面条总也吃得很慢,他依然很瘦。 妈妈买回了一些小鸡,放在了一个很大的竹筐里养着,竹筐就放在了门口。每天放一些煮熟的小米让小鸡吃。少年也学着妈妈的样子,站在竹筐旁边,边撒些小米边看着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啄米吃。有时那些小鸡也会歪着脑袋,仿佛看着少年似的。小鸡黄澄澄的绒毛,摸上一摸,暖融融的感觉令少年很喜欢这些小东西。家中除了养的这些小鸡之外,还有一头牛。牛的力气很大,每天给它拌草拌料,吃饱之后就栓在屋后的一根大柱子上。站立了一会儿,它就卧在了干净的地面之上,嘴不住地动着,长长的尾巴甩来甩去,好赶去那些可恶的苍蝇。 天越来越热了,田间的农活也渐渐地多起来。爸爸妈妈每天要去田间干活,家里的东西就有放学回家之后的少年兄弟二人看着。弟弟还小,很多时候就得哥哥多做些事情,喂鸡,喂牛。此时,少年也慢慢地学会了做一些很简单的饭食,比如煮米,热馒头,甚至擀面条,但刚开始少年是赶不出像样的面条的,所以不得已改成了面皮。煮熟之后,爸妈从田间归来总也很欣慰似的。再后来少年不仅学会了擀面条,而且也能够烙饼。虽然方法有一些不正确,但他是思索着做的。 麦收季节到了,学校里也开始放假。爸妈去田间收割麦子,少年就总是与弟弟待在家中。他一方面看到弟弟,一方面还要照看着家中的东西。有时候妈妈会在下午做馒头,发酵之后的生面中张开一个一个的小口。妈妈把面块全部放在了案板之上,一整块的面,在妈妈手中,很快就成为一个一个的小面剂儿。白白的,具有一样大小的面团等距离的整齐摆放在锅盖之上。妈妈把洗干净的抹布盖在了上面。妈妈告诉少年,她要去地里干活,看好这些刚剁好的未蒸熟的生馒头。 少年站在屋后看着妈妈的背影。阳光还很是强烈,道路两旁的高大树木遮挡着阳光。妈妈的背影,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暗了下来,但也很快地就进入了一个拐角,消失在少年的视线里。少年扭回头,此时道路上零星星的有些干活的农民,他们戴着草帽,扛着或握手中的农具走向田间。金色的麦浪中细细望去,那毛茸茸的麦芒之上像是浮起了微微的波浪,一条条的水纹似的曲线悬在空中,也消失在了耀眼的阳光中。牛正老老实实地卧在树荫之下打着盹儿似的。不远处的几只小羊,悠闲的吃着路边的树叶。小河中的水鸭子嘎嘎嘎地叫着。少年蹲在了路边的土地上,他捡起一块小石子,低头在地上任意地画了起来。他画了好多的东西,有的是图画,有的是一些文字。他觉得腿有些发麻,于是就站了起来。两条腿像是没了知觉似的,他哆嗦了几下,慢慢地转回家去。刚转过屋角,眼前的一幕令他惊呆了。他开始大叫起来,原来有几只小羊正在厨房内,没蒸的小馒头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地上拉拉扯扯的面泥凌乱一片。他使劲赶跑那些可恨的小羊,很着急也很害怕似的。他开始整理那些面泥。案板之上的面团已经为数不多,少年轻轻地揪掉地面之上的面团脏的部分,把干净的面泥放到案板之上。他思索着,他开始学着妈妈的样子,做起了馒头。把面块揉捏在一起,可是手上沾的都是。他想起了妈妈做面食时常常用一些干面粉。于是他抓起一把面粉撒在上面揉按起来,果然好多了,他边做边想着,可总算能把面揉捏在一起,成为一束。他拿起菜刀,两只手轻轻地很小心地在上面按压。他还不能像妈妈那样大刀阔斧般地梆梆梆地剁下来。如果说妈妈是在剁馒头,而他顶多算作切馒头。少年切出来的面团大的大,小的小,实在没有妈妈做的好看,可也总算是弄好了。他也学着妈妈的样子,换了块干净的抹布,盖在上面。他洗了洗手,之后关紧厨房门走进堂屋,见弟弟还在熟睡。 少年看看竹筐中的小鸡,他也数了数。他给小鸡撒上一些小米,在那只小碗中添加一点水,他看着小鸡喝水吃小米。此时竹筐中发出一种略微刺鼻的气味,他站起了身走向里屋。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弟弟也像是醒了过来,而屋子里好像更加的黑暗了。少年坐在床边,他望望房顶,一会儿又看看那几乎空着的一口囤。他想起了老鼠吃麦子的情形,但此时他的心理仿佛涌出一丝难过,天真的要黑了下来,爸妈还没有回来,他的心里更是极度的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他想起了电影中的蒙脸贼人,他甚至都不敢呆在黑乎乎的屋子里。他扯着弟弟的手来到了屋外,站在了屋后的道路边,这里好像明亮一些,但远处也看不太清一些东西。田间的农人已陆续地归家。少年望着那些行人们,从他们中间寻找着爸爸妈妈的身影。少年好像一次一次的不住的失望。他与弟弟像是叫喊起来,在喊叫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两个还很稚嫩的声音越来越高,他们不知道爸妈能否听到他们的喊叫。天已黑得都看不清对面的人,此时爸妈终于回来了,弟弟像哭了似的,少年哆嗦的心也稍微安静一点。他们与爸妈回到院子里。此时一种很凄厉的尖叫声传来,妈妈急忙跑向鸡筐,少年也跟着跑来。竹筐中的小鸡死了好几只,原来是被老鼠咬死啦。妈妈开始责怪起来,她抚摸着那几只还活着的小鸡,然后抓起那几只死了的小鸡走开了。少年僵直地站在那里,他仿佛感觉到了妈妈像是向厨房走去,他更加害怕了,害怕妈妈更厉害的责怪。果然妈妈发现案板上面的面块不是原来的样子,便问起了少年,他不得不把羊吃面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正要再一次的责怪起来,见那几块大大小小的面团之后,心里好像知道些什么似的,只是问了一句:“这是你做的?”少年轻轻地“嗯”了一声,低下了头,不敢看向案板。他好像听到了妈妈只说了一句,“可别把羊给撑死了!” 屋内亮起了油灯,少年这时才想起,刚才怎么忘记点灯呢!他看向竹筐中,此时竹筐已被妈妈搬到了屋子里。那几只小鸡像是紧紧地偎依在了一起,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啾啾声,惊恐万状般地把头埋得很深很深。 第二天的一大早,爸妈依然是早早地起床。朦胧中,少年仿佛听到了妈妈的一番嘱咐。之后,耳朵中只剩下广播中响起的音乐。天亮之后,少年起床做上早饭等着爸妈。此时少年好像想起了爸妈安排的事情。他来到了牛屋,刚打开屋门就发现那牛竟然前腿站在了牛槽之上,瞪着两只明亮的圆圆的大眼哞哞哞直叫唤。少年拿起拌草的棍子赶牛下去,那牛伸着大头撞了起来,并不住地发出哞哞之声。少年这才发现,原来那牛鼻子上扎着一个金属环,绳子就系在上面一直拴向槽子旁的柱子上。少年见槽子中空空的,他想大概是牛饿了吧。他赶紧抱起铡好的干麦秸放在牛槽旁的大水缸中,搅动几下之后捞了起来,倒在牛槽中,并撒上一些料粉,使劲拌动了几下。那牛竟像是与他抢着似的,把头伸向槽中。少年见牛吃了起了草,也安静了下来,他也很放心地离开。 牛是早上与上午吃草料,到了下午就要被拴在屋后的木桩子上。它站立了一会儿之后就卧了下来反刍。它的大嘴上下有节奏地动着,一张一合的,有时也好像左右微动。它的湿漉漉的嘴角冒出了很多的白色的泡沫。它不在瞪着大圆眼,很安详地摇动着尾巴,注视着前方像是很享受似的。 到了傍晚时分,少年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看向木桩,发现牛不见了。于是他开始四处找起来,口中发出唤牛的声音,就像唤羊似的,但怎么也见不着牛的踪影。少年走在大路上,见有小牛的走动,但那不是他家的牛。少年一直走了很远,他来到一条河的旁边,见他家的牛正站在河底,离水很近的地方。他有些害怕,害怕牛会掉入水中淹死。他慢慢地走近牛,站在河岸上开始唤牛,那牛牛看了看他像是不认识似的,掉头又跑了,一直跑上了岸,又向远处跑去。少年也跑着追赶,牛的力气可真大,少年怎么也赶不上它。渐渐地,牛已跑得很远,它跑过桥去到了河的对岸。那里有很多坑坑洼洼的空地,还有几座很高土窑。少年也向那里跑去,他从地上拾起一根棍子,叫喊着示意牛能回来。那牛像是故意惹人生气一样,朝更高的土窑上跑去。这时已有大人帮忙,他们边询问少年,边帮着去抓牛绳。几个大人终于拦住了牛,抓住了牛绳。少年早已气喘吁吁,心惊胆颤般地接过牛绳,慢慢地赶着。那牛大概是害怕少年手中扬起的棍子,又伸着大头使劲跑,少年两只手紧紧地抓着牛绳子,却跟在了后面,牛拉着少年跑了起来。少年真害怕抓不住绳子,牛会再次跑掉。于是用另一只手努力抓向绳子更长的地方。他虽然跟在后面追跑,但他也很努力让牛朝家的方向跑去。可是他的很瘦的身子根本就做不了主,还是在大人的帮助之下,少年才松了一口气。那人是认识少年的,他边询问少年,边抓住了牛绳。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牛绳到了他的手中,那牛仿佛老实了许多。少年跟在后边,到了家里,此时天已很黑,爸妈也从田间回来了,与那人说了一些很客气的话。那人离开之后,爸爸把牛牵回屋,拴在了牛槽旁的大柱子上,并说了一句:“有劲儿,打场的时候就让你出出力!” 6。 田间地面的麦茬之上躺着农人们用镰刀割下的麦秧。人们用木板车一车一车地把这些麦秧拉向打麦场。满满的一大场的麦秧堆的老高。头戴草帽的老农牵着老牛,拉着一个石滚碾子在上面转了一圈又一圈。不多时高高的麦秧就变得很薄。农人们手握大杈,把麦秧翻了一遍之后,准备再一次地碾压。老牛累得张着大鼻孔被拴在了路边的树荫下喝着桶中的清水。第二遍的碾压之后,很多人一起手握大杈翻着麦秧,并把麦秧一堆一堆地在场边垛起来。剩下的就是麦糠与麦子了,在一个适当位置,把这些东西弄成一个大堆,趁有好风,善于扬场的农人,紧握木锨,一锨一锨地扬起来,从空中落下了如皮肤颜色一样的小麦子,麦糠被风刮向的另一边。有时麦子砸向草帽发出啪啪啪的响声。麦子越来越多,麦堆也越来越高,农人们劳动着,同时也说笑着,热热闹闹的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息。 少年掂着一壶温开水向田间走去。他来到打麦场见着妈妈正双手攥着扫帚把扫着麦子堆上的一截儿一截儿没有被风吹走的麦秸,而爸爸正站在麦堆的一端扬着麦子。爷爷是扬麦子的老手,他正站在那一端,戴着灰黑色草帽头也不抬地趁风扬着。妈妈最怕口渴,少年把水壶交给了妈妈。妈妈说:“等会儿再喝”,边说边把水壶递给爸爸。爸爸说:“让咱大先喝吧”,边说边把水壶给了爷爷。爷爷说:“风正好,先扬着吧!”,最后水壶又回到了少年的手中,少年放下水壶,用小笤帚扫起了落在了远处的麦子。 干干净净的麦子被装成了一袋袋,装在了木板车子上,妈妈在前面拉着,少年就站在后边使劲推着。他的两手放在了温热的装满小麦的袋子上,他弓着腰,伸着头,脚底紧紧地蹬着地面,木板车向前慢慢地移动着,发出吱吱的响声,仿佛也很用力地承载着这一袋一袋的麦子。 在收割麦子的过程当中,往往也会遇到下雨的天气。这样的天气里农民们往往会更加的繁忙。越是下雨,他们越拿着塑料布跑向田间,跑向打麦场,防止雨水淋坏了他们即将收获的果实。等到小麦收割完打出麦子之后,田间的墒情依然很好,农人们也赶着种玉米、芝麻、花生、大豆等秋季作物。少年已能够随同爸妈去田间种玉米了。他一手端着一盒玉米种子,另一只手拿着尖尖的金属棍儿,少年学着爸妈的样子,蹲在地上,在麦茬中间的土壤处,用这尖尖的利器使劲扎去,翘起,然后把两颗玉米籽儿放在里边,并放下土层。每隔一尺长的距离就埋上两颗玉米籽,就这样从田地的一头一直到田地的另一头,反反复复,只蹲得他腿麻腰疼。实在难以坚持了,少年就站起身子,捶捶自己的腰,捏捏自己的腿,然后接着蹲下来继续往土中放着玉米籽。少年是干不了几场这样的活,因为学校已经开学,少年每天去了学校。每逢星期日的时候,妈妈想着让少年干些简单的农活,但是一到星期日的时候天又老是下雨,一家人只能待在家里。妈妈因此也常常说:“恒这孩子真有福,一到星期天就下雨,这是老天爷舍不得让你掏力气干活儿啊!” 一场一场的雨水的滋润,田间已经是青青一片。农人们开始除草,他们扛着锄头来到田间,弓着身子锄去玉米苗间的各种杂草。他们甩着汗水,并不住地弯下身去捡拾那些杂草,或者拔去较稠密的玉米苗。从这样的场景中,少年想到了他学过的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的,他每天见着妈妈从田间归来,妈妈放下锄头的慢慢动作中,那半弯着的腰一定很疼,少年是这样想的。 六月的天气是一年中最热的,而学校里已经放了暑假。少年可以待在家里,也不断地听从爸妈的安排。此时,家中的那头牛也闲了下来,小鸡渐渐地长大,长大到不能再放在竹筐中,被放了出来,在院内任意地跑着。妈妈担心这些小鸡跑丢,于是就在这些小鸡的身上染上颜色,那红红的颜色挺好看的。每天晚上,这些小鸡又回到竹筐的周围,但此时竹筐早已被妈妈放在了一棵树的下面。这些小鸡在树底下朝筐中飞去,进不了的小鸡就卧在了筐的边沿之上。小鸡中的某几只开始扇动翅膀,而且头顶上的鸡冠越来越大。妈妈说,这是几只公鸡,该上树了。妈妈抓起这些小公鸡,放在树杈之上。小公鸡又飞了下来,妈妈再放,反反复复的好多次之后小公鸡才开始适应下来,由站在这个树杈上又飞到另外一个树杈上。而后来的每天晚上,妈妈不再这样帮小公鸡上树,这些小公鸡自己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往树上飞起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天刚亮的时候,这些小公鸡开始叫起来,少年听得很清,他认为这些公鸡的打鸣声很好听,甚至好听到都能与黄鹂的叫声相比。只是公鸡的叫声更响亮,更高亢。有时在白天,少年见着地上跑着的大公鸡,也会不断地叫几声。大红的公鸡昂起高高的头,伸着长脖子,张着尖尖的嘴,那声音仿佛是从肚子到脖子,然而直冲向它的头部似的。嘹亮的声音能听得很远,这时少年想起了在戏台上的有些演员,抹着红红的脸,挂着很长的胡子,很卖力地演唱。那豪迈的唱腔中好像在显示着他的凛凛威风。这高傲的大红公鸡在家禽中一定是最厉害的,它是家禽中的“红脸王”。 天热得实在太很,到了晚上,屋内的蚊虫也多了起来,人在屋内休息头皮胀得发麻,简直就要喘不过气来。人们就在外面的院子里休息。有的躺在一张木板床上,有的干脆就在地面之上搭起了地铺,铺上几张席子,上面铺上被褥等。为了防止露水的浸湿,他们在上面支起一块塑料布,一家人躺在院子里的地铺上确实凉爽许多。到了夜间,甚至有些冷,所以只能盖上被子。每天晚上少年躺在他家院中的地铺之上,侧面望着遥远的星空,有时赶在有月亮的晚上更是喜人,因为整个院子里都明亮亮的。少年静静地躺着,一家人议论着话语,他甚至都能听到邻家人的说话声。有时外边也是有蚊虫的,嗡嗡的在耳边响着。少年把一把扇子放在了自己的枕边,好扇去那些可恶的东西。同时他也会在自己的旁边放一根棍子,因为他担心小羊或者老鼠打此经过。一旦有小羊或者老鼠来了,他会拿起棍子使劲地敲击着地面,好吓跑这些小动物。宁静的夜晚里人休息了,但是小动物们却依然活动。所以少年以为宁静的夜晚并不安静。有时在晚上村子里放电影,或者有敲着牛皮鼓打着快板唱小戏的,热闹了一阵子之后,人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在路边有躺着的人,那一明一暗的烟头火光里不时发出哼哼声或咳嗽声,那大概是提醒走着的人,小心别踩着了,这里睡的有人。 白天,少年坐在院子里,他望着院中的每一棵树,最高大最粗壮的要数东南角的那棵大楝树。妈妈说是等孩子长大了,为孩子做大床用。这棵树下楝枣子落得满地都是,只是那些椭圆形的如小拇指头一样大小的绿色东西气味很难闻。少年不爱玩它,但他听说这些东西埋入土中,会长出小树苗的。少年没有种过这种小籽粒儿,但他也确实见到在大楝树底下或墙根处有很多小小的楝树苗。强烈的阳光下,知了的叫声更加响亮,而且这里一阵那里一阵的像是很壮观的一组乐队在演奏交响乐。那树干之上有很多蝉蜕,少年很容易捏起低处的蝉蜕,至于高处一点的蝉蜕,用一根棍子也能敲打下来。据大人们所讲,这东西可入药的,拿到药铺能换钱的。少年也试着积攒了许多这些金色的外壳。弄了一竹篮,的确能换作几角钱的。院子的东边有一棵榆树,榆树的外皮更加斑驳,裂着很大的口子似的。村子里往往也有一些叫卖声,或收或卖的各种声音很响,足以响彻整个村子。那大概是他们长期的叫卖实践的结果。据爸爸所讲,榆树皮是可以卖掉的,所以少年听得真切,那些叫卖声中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收榆树皮喽!但若要卖榆树皮必须等到砍倒树之后,把树皮刮下来才可以。不然,好好长着的一棵树被剥掉了皮,那树会死的。少年心想榆树真够可怜的,死掉之后竟被人们剥得连皮都不剩。其实看着这棵榆树,少年想到的是每年春季时分,榆树枝上长满了榆钱,折下一枝枝来,用手一捋,放入篮中,淘洗干净,蒸入锅中,不失为一种美味。而现在少年看着这棵榆树,他发现的是树干下地面上有些很小的小孔,轻轻抠一下,小孔越来越大,勾出一种叫做爬蚱的小动物,很多孩子拿此动物烧着吃,而少年却把它们盖在一口碗下,一两天后掀开碗来,这些小爬蚱变成了一个一个能扇动翅膀的蝉。只是身子还有几分的肉红,看上去挺好看的。少年把它们放了出去。他不知道这些可爱的小生命,能不能加入到那庞大的“乐队”中去。但他确实已经放走了他们。 一阵阵的蝉鸣在整个的白天几乎是不间断的。轻柔的微风撩拨着还很繁密的枝叶,让人们不会因天热而心生躁动。地面之上飘零的落叶也仿佛告知人们最热的天气即将过去,凉爽的秋很快就要到来。少年在不经意间觉得自己的后脑勺处有些轻微的疼痛。他用手摸去,感觉出像是有一个小疙瘩,暂时没有理会它。但是几天之后就越发的疼痛。他借着一面镜子看了看,那个疙瘩挺大的,几乎成为了一个脓包。他不敢用手碰着,因为那的确很疼。爸爸说:“这是要成了疮的,必须得煞掉。”少年不知道怎么个煞法。他听着这个词,心里很不好受。他忍着疼痛,忽见爸爸在一块石头上磨着一根锥子一样的铁东西,那东西的头尖尖的,稍微有些明亮。爸爸对少年说:“我趁你睡着之后就用这个尖锥子扎向脓疮,把脓水挤出来。”爸爸边说边在少年面前展示那个很尖的东西。少年听完爸爸的话之后,一股血直冲到头上,脑袋钻心地疼。那种撕裂般的疼痛,仿佛直戳到他的心脏,他真是吓得要命。他甚至都不敢睡觉,只是傻傻地坐在地铺之上。他想象着那个尖尖的利器,如何狠狠地扎向他的头部。他又是如何咬牙切齿般地忍受着。他一句话也不说,就只是坐着,他也不敢说话。 这天的上午,爸爸领着少年来到了村卫生室。爸爸对少年说:“还是让医生给你把脓疮割下来。”少年不敢走动,但又不得不走动。他离爸爸好像很远,但最终还是走进了卫生室。他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他不敢看医生。他实在是害怕医生手中的刀,虽然还没有见着医生手中的刀,但他想那一定是一把非常锋利的明亮的尖刀。他早已吓得低着头,屋子里乱糟糟的声音压抑得他喘不过气来。闭上了眼睛,任由头部钻心地疼。他仿佛感觉到了医生在摸他的头部。他开始大声哭叫,握紧拳头不住地摆动起来,整个身子像是在颤抖。哭声还没有结束,医生说:“好了,包一下吧!”怎么?少年有些怀疑,除了一直的疼痛之外,没有别的特殊的更令人难受的感觉。他止住了泪水,仿佛听着医生说了句:“咋吓成这样,过几天就好了。”少年站直了身子,但他依然低着头,不敢看人,只是看着自己汗涔涔的手背。他有些害羞,他是因为刚才的大声哭叫而害羞。他又想着,煞疮是怎么个一回事?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的疼啊!他是因为爸爸最初的话语以及那个磨的光亮的锥子而吓得惶恐不安了好多天。 心惊肉跳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少年或坐着或站着,总是默默地待在一边。他想着,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爸爸为什么用一个锥子吓着他?他实在想不明白,也更不敢去问,只是让这件事在自己的心里慢慢地沉淀下去。也让那些不快乐在心中慢慢地自我消化。 胆怯的心理往往不是出自于自然,而是来源于人为。头部不疼了,纱布也很快地揭了下来,只是那里出现了一个凸起的疤,一个永远的疤痕。 作者简介 李红卡,年出生,河南省沈丘县教师,文学爱好者。 香落尘外书斋——香落尘外平台团队 特邀顾问:乔延凤桑恒昌 名誉总编:赵丽丽 总编:湛蓝 顾问:王智林/李思德/李国仁/杨秀武 总监:徐和生主编:烟花清欢朱爱华锦 总策划:崔加荣策划:柳依依暖在北方胡迎春 编辑:陈风华莲之爱风碎倒影连云雷朱晓燕 播音部: 主播:魏小裴自在花开眉如远山西西 理事单位: 广西北流市十字铺工业园松林瓷业 投稿须知: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tongpizw.com/htpzy/10901.html
- 上一篇文章: 海宁梅里达花园梅里达花园欢迎您官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