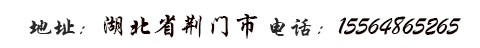高位截瘫病人诗意的一天
|
母亲、红辣椒和猫,生活的仪式感和幸福感,在母亲的生命里,洇成一副画。 我的一天 渴望 文 一、早晨,我生命力量的开始 天蒙蒙亮,母亲就起来了。母亲不用闹钟,她的身体,就是闹钟。我看了看时间,早晨5:10分。秋凉了,窗外亮得比夏天晚一些。十五年了,母亲早起为我翻身,已成为她生命中的习惯。母亲心疼儿子,知道儿子一夜睡觉的姿势不变,会很难受。母亲疼在心里,为我翻身成为母亲起床后的第一个生活的仪式。 帮我翻完身后,母亲的手,在我的右肩上拍拍,这是一天中,我生命力量的开始。随后,母亲拿着笤帚,朝屋里、屋外打扫一遍。可这土屋,总也打扫不干净,房顶的土块总是往下掉,像下雨一样,还有木头上被虫子拱的木屑,飘的到处都是。母亲扫完地,再把桌子柜子上用抹布擦洗一遍。在母亲心里,这房屋虽简陋了点,可也是遮风挡雨的家,总会尽力把它拾掇得干净些,我们住得也舒适一些。 拾掇完屋子,母亲就去鸡舍把鸡放出来,在院子里撒些玉米粒,边喂边数,生怕少了。这些鸡,母亲把它当做心肝宝贝来喂养,指望着它们下蛋来给我补充营养。这些年,鸡蛋是家里唯一的最好的营养品了。母亲把鸡蛋都留给了我,把辛劳和汗水,留给了自己。 我的父亲母亲,不到过年过节,是不会吃一个鸡蛋的。 干完这些,母亲就开始进厨房做早饭了。早饭经常是烧些玉米糁子汤,或是大米汤,再摘点豆角,青菜,辣角调拌点菜,就着蒸馍,一顿“母亲牌”早饭就这样热乎乎的端到我的床前。侧卧在床的我,用勺子慢慢的吃着,想着,也思考着:不知道,和父母相依为命的日子,还能有多久。当我突破了自己,坦然的接受,“不赶路,不着急”后,我更珍惜和父母在一个屋檐下的日子了。 马尔克斯说,如果父母健在,你和死亡只隔着一层垫子。如果父母没有了,那层垫子就被抽走了,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我和双亲在一起生活,我的内心很圆满。 二、母亲的“小跟班”,和母亲互为影子 中午,母亲把我放到轮椅上,推着我到屋檐的台阶处,这里是我患病以来仰望世界的起点,也是我每天“活动”的终点。台阶一侧的墙壁上,红辣椒被母亲一串,挂起来,给土屋增加了亮色,红彤彤的日子,除了过在心里,生活也被母亲过出了仪式感。这时,母亲的“小跟班”就跳上小板凳,懒洋洋的躺在小板凳上。一会儿闭眼静卧,一会儿翻过身来,用舌头舔一舔爪子,挠一下痒痒。看到母亲的手动了,再伸长脖子“喵、喵”的叫两声…… 养猫,已是母亲习惯了。从我记事时起,家里永远有一只猫。只要家里的猫老死了,或病或吃药死了,母亲都会念叨好久好久…… 猫是母亲的孩子。 去年,母亲养了一只狸毛,全身上下纯狸色,毛色虽不讨喜,可非常的好养活,无论什么饭都吃,长的也快,还很勤快,每天晚上都能逮到老鼠,自家逮的没有了就去邻居家,坡地里逮。可是,不久后突然不见了。母亲四处寻找,最后,在屋后面发现早已死了,估计是吃了不知谁放的鼠药了。为此,母亲伤心了好长时间。没有猫的日子,母亲感觉生活中失去了什么似的,她的神情黯然失色,有时候还背着我偷偷的掉眼泪。 农村的土房子,离坡又近,若不养只猫,老鼠是不分穷人、富人的,不会在穷人家少吃一点,在富人家多吃一点。只要有吃的,家里的粮食很快就会被老鼠吃光。 今年三四月份,母亲又从邻居家抱了这只小花猫。谁知,这只小猫馋嘴的很,吃东西挑三拣四的,没过几天就瘦成了皮包骨头。母亲常抱怨:“人都没有肉吃,你还想吃好的……”但母亲又不能没有猫,眼看小花猫坚持不下去了,正好母亲把仅剩的两根火腿肠调菜给我端到床前,小花猫闻到了一摇一晃的跑了过来,扬起头“喵、喵”的叫着。我等母亲转身出去后,就用勺子把火腿肠压成小块,一块一块的把火腿肠给小花猫吃了。 还别说,自从吃那两根火腿肠后,小猫咪渐渐的吃起了饭,走起了猫步,更有了精神。过了几天,又开始活蹦乱跳了。 父亲多数在地里或坡上,家里经常就我和母亲两个人,我无法移步,小花猫代替我,帮我做我不能做的事。母亲进屋,它跟进屋。母亲去厨房,它跟进厨房。母亲独对夜空,猫也独对夜空。母亲来给我翻身,猫就蹲在旁边,像个听话的孩子,两只眼睛滴溜溜的看着…… 母亲和小花猫互为影子。 我也经常说母亲:“小花猫就是您的‘小跟班’呀”。 其实,我时常听到母亲和小花猫念念叨叨的说着话,交流着……有时还真以为母亲身边多了一个亲人。 母亲串着辣椒,小花猫懒洋洋的躺着,我则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不知不觉快中午了,母亲起身开始做饭了,小花猫便跟进厨房里,时不时“喵、喵”的叫着,像是在告诉母亲:“做饭别忘了我哟。” 三、母亲把心愿放进了月饼馍里 临近中秋节了,母亲忙碌了起来。 中午饭,母亲简单的煮了三小碗汤面条,我,父亲,母亲每人一小碗,调上辣子,酱油,醋,再拌上萝卜英子酸菜,就是一顿热乎的午餐了。小花猫不停地在我和父母跟前转来转去地要吃的,它跑到我跟前,扬起头“喵、喵”的叫着,我笨拙的手握着勺子给它弄了点面条,可它闻了闻,嫌弃我似的转头就走了。 母亲边吃饭边唠叨着父亲:“我吃完饭要蒸馍了,你整天转悠,柴也不劈,一会都没菜烧了……” 父亲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唠叨,也不会回应母亲。他知道,每当临近节气,母亲都会这样的,也不是没有柴烧,其根本原因还是要过节了,要买一点生活用品,改善一下,有个过节的样子。亲人之间的念叨,无论怎么重复,都觉得很亲。这就是生活的样子。絮絮叨叨的念,平平淡淡的过。我的父亲,懂得生活的哲学和相处的智慧,他知道母亲喜欢念,他就沉默,或者顺着我的母亲。 自从我病倒后,家也不像家了,逢年过节更谈不上什么节日的气氛了,反倒是平添了许多烦躁和愁绪。眼下又到了中秋节,心中的惆怅不请自来。我躺着这十五年,除了夜晚失眠时,透过窗户仰望过苍穹,我似乎很少去注意八月十五的月亮。总觉得月亮的阴晴圆缺,已与我无关。中秋节,在我生命的日历上删去。 我拿着手机,毫无目的的划拉着。父亲在院子里劈着柴,本来个子不高的他,双手握住斧子吃力地晃动着,我看着那瘦小的背影,不由得眼睛湿湿的,我的老父亲,一辈子闲不下来。 无论现状有多么的不堪,母亲也要把日子过出诗意来。母亲同许多年前一样,在厨房里忙碌着象征团圆的甜甜的月饼馍。母亲那佝偻的身影不停地在厨房里晃动,依旧是红糖拌核桃仁包的圆圆的月饼,依旧是热腾腾的散发着香味…… 在母亲的心里,永存一份企盼:天上月圆,地上人圆…… 普天之下,千万个家庭,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个待圆的梦。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有着不同的心愿。也许这就是人生。月圆的内容,被母亲包进月饼馍里,被我的右手的食指敲进这简短的文字里。 四、夕阳也是旭日 母亲把月饼馍蒸进锅后,太阳快要落山了。“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受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颠布散烈烈朝辉之时。”太阳的下沉,也提醒我该回屋休息了。微风吹起了凉意,母亲走到我身边,为我整理衣角。母亲生怕这些许寒凉的秋风把我吹感冒了。她知道,久病的我,身体抵抗力很差,稍有不慎就会感冒发烧,一发烧就会引起褥疮的严重和并发症。这对一个风雨飘摇的家,更添一层霜。 母亲把我放上床安顿好,从厨房里端来刚出锅的喷香的月饼馍放在我床头前,母亲说:刚蒸出来的,你吃一个吧。我看着母亲,轻轻点了下头。其实,这些年,无论春夏秋冬,我们每天都吃两顿饭。母亲拿来热气腾腾的月饼馍,嘴上也想吃,可胃消化不了,又不好拒绝母亲的心意…… 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暮色,我蜷缩在床上,母亲忙碌的脚步声在耳畔回荡,中秋更添回忆、愁绪与人生况味。欧阳修说过,人远天涯近。那些抛弃我的人,始终在远方,和我靠不了岸。那些天涯海角的事,在我的窗前不请自来。于天涯咫尺间,我与父母相守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情,人间的至真至爱,会不会与今夜那轮皎洁的圆月重逢? 这十五月圆的夜晚,如水的月光,和我家暗淡的灯火连成一片。 (风铃摄于若尔盖) “一天很短 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 就已经手握黄昏。 一年很短 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窦绿, 就要打点素裹秋霜。 一生很短 短的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 就已经身处迟暮。” 作者·简介 渴望:本名毋宝群,70后,河南三门峡人。灵宝市作协会员,《云水涧》原创文学平台总编。一个热爱文学的农者,作品散见于公众平台和纸媒。本人颈椎骨折压迫神经致高位截瘫,瘫痪在床已十五年,且伴有并发症。雪砸在我的身上,但我要拼尽全力,把覆盖在我身上的雪,一点一点抹去。我选择了文学,我要在苦难的盐碱地里,提取生活的甜。写作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但能安顿我的灵魂。 更多阅读推荐 渴望 曾经,他走在朝霞的前面;如今,他已向生活低头 渴望 我瘫痪卧床后,只有回忆带着我,重返新疆,重返记忆深处 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tongpizw.com/htpyl/6763.html
- 上一篇文章: 民间偏方一法师赠我的中医名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