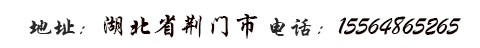家乡的火晶柿子
|
白癜风医疗 http://pf.39.net/bdfyy/index.html 家乡的火晶柿子 文/姜永学 儿时记忆除过母亲甘甜的乳汁就是家乡红红的火晶柿子,是当年母亲平息我因为饥饿时常哭闹的秘密武器。 半棵火晶柿子树 随着长大,火晶柿子的记忆变成了村西三大后墙外那半棵火晶柿子树。只所以是半棵树,是因为爷生养了两个儿子,父亲和三大。两兄弟成家后另立门户,而爷只传下来这一棵火晶柿子树,当然就要分成两半。 说来也巧,也许是天意,这棵树从根部自然分成东西两个主干,高低粗细肉眼根本看不出差别。三大和三娘一合计选择了东面一半,理由听起来也很合理,东面朝着他家后院看护方便。也是,那时候日子紧,吃的短缺,柿子刚有形,味道还很涩很难吃就有孩子摘食,当地人俗称“害娃”。母亲虽说不善言语,心里很亮堂,她说其实三大主要是因为西面朝着村外,紧挨着路,来来往往都是人,伸手就能够着,遭孩子“害娃”那是免不了的。实际也真是如此,往往等不到成熟,我家树下面那一层密密麻麻的柿子早早就被洗劫一空了。 但后来的情况却有些没想到,靠东的那一半虽说少孩子“害娃”,但树冠紧挨着三大家的房屋,加上心沉的三大在房前屋后栽满了桐树和槐树,高大的树冠像一把把巨大的伞把东边的那一半柿树严严实实遮在下面,不采光通风也不好,并不怎么好好结,一年也卸不了多少柿子。反倒是西边我家的那一半树,面对着村外开阔敞亮,阳光和透风都好,柿子常常结得疙里疙瘩像蒜辫一样,害得三大一家人直眼红后悔。 分成两半的柿子树虽然下面主干分明,但到了上面枝叶盘绕交错,采摘时稍不留神就会出错,因而常常会引发我姊妹和三大家孩子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经常会上升到三娘和母亲之间,给父亲和三大两兄弟带来难以应对的纠纷。常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最后往往是仗义疏财的大伯从自家拿一蛋蛋笼火晶柿子来做平息。常常是三娘连笼拿走还一脸的不悦意。 大伯是大爷的独苗,所以没有把树分成一半的烦恼。大爷和我爷也是亲兄弟,但不公平的是大伯家里却有八棵和我家连成一片一般大的柿子树。除过一棵青柿和一棵赦黄外,其余全都是火晶,从树龄来看全都是祖上传下来,足见先祖们对火晶柿子的偏爱。 卸柿子 对于火晶柿子的记忆接下来就应该是采摘,当地人俗称“卸柿子”。每年过了国庆,我就迫不及待嚷着要卸柿子,一方面是自己嘴里痒痒,蛰伏一年的柿子虫被红红的火晶柿子唤醒,在胃里抓得慌。另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一放学树底下站着的一堆又一堆大小不一高矮不等胖瘦各异的孩子,像码头上堆放了一地刚从轮船上卸下的杂物,怎么赶都赶不走。有爬上树摘“蛋柿”的,有站在下面仰着脖子嚷着看的,有用木棍或竹竿打的,还有用土块或石头塌的。大人来了喊一声四散而去,走了他们又回来了。地下常常是一地的跌伤的生柿子以及咬了一两口扔掉的半拉柿子或厚厚的柿子皮。埋藏在内心说不出口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一定要卸在三大家前面,不然我们家就会少卸很多柿子。但憨厚的父亲老说太早,柿心还没开,也没上霜,开了心经过霜的火晶柿子耐放也最好吃! 火晶柿子皮薄瓤嫩,所以很娇贵,有不得一丁点碰伤,不能跌落在地上。而柿子树的枝干很脆弱,极容易折断出现危险,所以卸柿子绝对是一门手艺活。 卸柿子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用铁钩勾,方法就是在一个长木棍或竹竿上固定死一个铁钩来勾柿子。具体说就是用铁钩勾住结着柿子的新枝,慢慢旋转,听到“嘣”的一声,树枝就折断了,然后移下铁钩取下枝条仍缠绕在铁钩上的柿子。这一过程一定把握好技巧,不要晃动,也不能转动手中的木棍或竹竿,要是不慎让柿子从高空跌落下来,就会四散而去,常常是摔得“头破血流”,坏了这一抓红红的柿子。因为柿子一旦碰伤还没暖熟,伤的地方就开始发酸不能食用了!这一方法最简单但效果最差最容易摔伤柿子。另一种方法就是用竹竿夹。取一根长竹竿,在细的一端用刀对开两个三四公分的口子,代替铁钩用来夹柿子,具体做法大致和铁钩相当,但因在旋转中挂着柿子的嫩枝会被竹竿口紧紧夹住,多了一层保险,相对来说比铁钩要稳妥很多,柿子不容易在半空跌落,所以伤损相对要少。 以上两种方法虽然省事,没有危险,也较省气力,但柿子伤损都大。最后一种方法比较麻烦但效果好,那就是直接用手去摘。有人说这不是废话吗?这里我当然说的是怎样才能做到用手直接去够去摘。拿一到两根大拇指粗细的绳子,越结实越好,最好是农村人常用的牛筋绳,说是牛筋绳其实是用牛皮合的。把绳子缠在腰上或着跨在肩上爬上树,把绳一端绑牢在一根树干上,然后牵着绳另一端小心地顺着形成整个树冠的主枝干缠绕一圈,或上下两圈,这个要依据树的高度和绳子的长度来定。最后用尽力气拉紧绳子,再把绳的这一端绑牢在同一个或靠近的另一个主枝干上。目的是把树的所有大的枝干牢牢捆绑在一起,像童话故事里十双筷子抱成团一样。这样采摘的人踏在任何一个大的树枝上,力量会通过绳子分散在其他相连的树枝上,排除了某一树枝承力过大而折断的风险。所以绳子当然要结实。 我家卸柿子,父亲采用都是第三种方法,实在够不着的边梢用前两种方法做辅助,死马当活马医,卸好多少柿子算多少。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不舍损柿子,另外也相对安全,就是前期准备工作有些麻烦。由于柿树枝干脆弱,即便用绳子做了安全防护,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采摘的人还是身量越轻越好,所以很小我就是最佳人选,而我也是乐此不疲。 我常常是胸前吊一个布袋,然后腰里系一根带铁钩的绳子像猴子一样爬上树,再把带勾的绳子放下去把笼吊上来,很结实地绑在一个粗的树枝上,开始卸柿子。这也是我最得意的时候,其时我就像戏里的主角,一家人都围着我转,三个姐姐、父亲和母亲都伸长脖子站在树下看,在给我叮咛安全的同时,不时提示着我的前后左右那里漏掉藏在树叶下的柿子。我则高兴地手摸着摘下一个个羞红了脸的火晶柿子,像是抓到了一颗颗有钱人家孩子含在嘴里,让我不住流口水的那五颜六色糖纸包裹的水果糖!卸满一布袋,我就爬回到笼边轻轻倒到笼里,再爬过去继续摘,笼满了我就用绳子放下去。常常是下面的三个姐姐和父母早已头仰得腰酸脖子痛,而我的兴致还正高。 虽然我家只是半个树,下面一层又常被“害娃”掉了,但在我记忆中常常还能卸不满一大老笼(很大的笼相当于一般笼的五六倍大)柿子。然后一家人换着手抬回去,小心翼翼放在自家的窑里面,接下来就只等暖熟馋嘴了。 后来姐姐出嫁了,我工作在外,父母也年迈了,我家那一半柿子就全让三大家卸了。记得有一年冬天三大家的兄弟孩子过满月,跑来给我报喜,大老远拿过一个牛奶箱,打开是满满一箱红红的火晶柿子,看着很亲切也很感动。堂弟说是我家树上卸的。这也是我家那一半柿子树留给我的最后记忆。现在村子早已淹没在经济大潮的拆迁中成为了回忆,那半棵柿子树和卸柿子的点点滴滴也永远只能是怀念了! 暖柿子和柿子醋 关于火晶柿子最深的记忆是对柿子暖熟的期盼和偷吃的贪婪。常常是还没放学心就跑回家里,老师后一半节课讲了啥几乎一概不知。那时的放学铃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百米冲刺的发令枪,我飞一样跑回家径直窜到窑里面摸柿子。 过去我们那儿主要是住窑洞。窑洞好,冬暖夏凉,但简陋不上档次。很少盖起的厦房,也就是关中八怪里的房子一边盖,只是作为富裕的招牌来给儿子引媳妇用的。老人一般都舍不得住,所以放柿子只能是窑里。过去窑里常有老鼠,从一家打洞到另一家,无所顾忌也从不差生随意出入。柿子是吃货,为了避免被胆大妄为的老鼠糟践,父亲便在窑里面用几根木头在空中搭起一个架子,上面棚上木板,然后铺上竹席。竹席四周用木板板或砖块支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凹槽像水池子一样,再把柿子一颠一倒一层层铺开。我常常就是顺着旁边搭着的木梯子爬上去,在灰暗的池子用手去摸,摸到软的就轻轻装在口袋,然后顺着梯子刺溜下去,皮都来不及剥,直接用牙很技巧地把外皮咬破个口子,嘴对着用劲一吸,那冰凉光滑的柿肉穿过喉咙经由肠道很顺溜地到了胃里,接着就是另一个,不一会几个柿子就全到了肚里。 就这样不知那不满一老笼柿子多少进了我的肚子。最后往往是某一天回来,正要再去捏柿子,一推开窑门,只见父亲沉着了脸坐在炕边,手指着案板上半生不熟的一堆柿子,像一个个泄了气的干瘪皮球,说:“看,这就是你一天到晚用手捏的结果!” 我前面忘了说,柿子的金贵和矫情还在于未暖熟之前千万不能用手来回地去触摸,否则摸成了老厚皮,就再也暖不熟了。 母亲在一旁总是和稀泥:“熟不了算了,正好可以做成柿子醋,咱还省得花钱去买!”然后母亲便把这些熟不了的老厚皮摘掉把儿,用清水洗净,凉干水汽,然后放在没淹过咸菜的黑瓷缸里,盖好盖子用泥把口封上。下来母亲就开始搬着指头数日子,一般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开封淋醋。这一天也是一家人最热闹的一天,迷信的母亲常常查着黄历算着日子,她说醋要好一定要找个黄道吉日。在选定的日子,打掉泥封揭开盖子,整个屋子就会飘满一股酸酸的香味,一团团细小的醋蝇好像在门外等候了很久很快飞进来,像初夏天空中飞舞的一波波蚊沫子,在人眼前来回晃悠着,母亲于是说好了。 一家人就又开始忙活起来,一般是父亲斜拿着黑瓷缸,母亲找出一块干净的纱布遮挡住黑瓷缸的下沿用来过滤,姐姐或者我端一个白洋瓷盆接在下面。眼看着白中带黄的液体从黑瓷缸透过纱布流到盆里,然后装满几个事先洗干净的葡萄糖瓶子,盖紧橡皮塞子,放在太阳底下晒,直到颜色由白变红最后成为深红色,这样柿子醋就做好了。母亲说这种醋越晒颜色越深味道越好。深红色的的柿子醋调在雪白的面条里,酸中仍带着柿子的香醇。这样作成的柿子醋常常由于太酸,食用时还要适当勾兑一些凉开水。母亲当年酿的柿子醋是我至今吃过最香的醋,无论是味道还是颜色都让人难以忘怀。 不光彩的记忆 后来在乡下工作,常看见有山里人挑着担子来卖火晶柿子,到了时节一街两行都摆放着带着淡淡一层白膜的火晶柿子。红红的柿子齐整地码在黑灰色的筐子或笼里,几乎成了街上的一道风景。深藏肚子里的馋虫瞬间复活了,时不时会不自觉地来到街上,买些火晶柿子回去,在寒冷的冬日围着火炉回味童年就早已铭刻于心的火晶柿子记忆。 记得很清有一次和同事老任出去溜达,当时天已接近黄昏,在街西头看见一位老人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没有系绑的帽扇在风中闪晃着像燕子翻飞的翅膀,瑟缩在一个角落卖火晶柿子,我的脚便挪不动了,要买火晶柿子吃。那时物价低,钱也值钱,一毛钱能买成十个柿子。我们一边吃一边和老人家拉家常,从哪里人扯到有多少柿子树,到家里几个孩子,再到一年秋麦两料的收成。吃了大半天临了算账,老人笑着说:“吃了这半天,两个小伙子才吃了这么几个柿子,你们城里人就是太讲究,爱干净,不会拨皮,还非要拨皮吃。”然后数着吃完的柿子把儿开始算账,不到三毛钱,我给了老人三毛,说:“不用找了!找几分硬币,装在口袋也时常弄丢了!” 老人家憨厚,一脸皱纹,欢喜地不住点头,又有些难为情,好像占了我们很大便宜似的,脸红得像笼里的火晶柿子,说:“这是我大老远用担子挑着来的,就挣个跑路钱。赶明格儿到我家里来,叫你紧饱吃,走的时候还一定要再给你拿些,自家产的不值啥钱”。 在回家路上,老任诡秘一笑说:“我把好几个柿子把儿踩在了皮鞋底下!”几个柿子差不多也不到一毛钱,大致也就是我多给的钱数,只是在心里上我总觉得我们偷了老人东西一样,但碍于老任的面子,我又不好意思说。后来我多次一个人特意绕到街西头,希望能再碰见那位老人,把钱补给他,但一直没能如愿。虽说那时都很年轻有理解和原谅的理由,但它始终是我火晶柿子记忆里少有的不光彩的遗憾。 缘起火晶柿子 有一个多年的异性朋友,算是红颜知己吧!相识也是因为火晶柿子。 她现在的家在西安碑林,老家是河南洛阳,大学毕业分配来的西安。起因只是因为庸俗又传统的一种婚恋方式:谈朋友也就是处对象。是在西安工作的同学乱点鸳鸯谱撮合的。于是她像嫁不出去的姑娘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似的,人生地不熟独自一人一路倒车从西安赶到我工作的乡下找我。当时交通或通信很落后,同学没有及时和我沟通好,她便来了,我当然没能去车站接她。 我所在的学校早年叫四中,后来因教改成了职中。也不知道是我还是同学没有把信息更新过来,于是她在镇上到处找四中找不着。眼看时候不早了,她找得也是又渴又累,看见街西头有人担担卖柿子,于是一边歇息一边买火晶柿子解渴。在卖柿子人的示范下,拨了皮,绵软细嫩的柿肉滑人口中,饥渴和焦虑一下子没了,不觉中几个柿子就下了肚,还不解馋,又买了一些,一边吃一边和买柿子的扯闲话。 “这是什么柿子?真好吃!”她问。 “火晶柿子,是临潼的特产。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卖柿子人说。 “对,我是来找人,你知道四中在哪儿?” “算你问对人了,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早年我兄弟在四中上学,我给他送过馍。这是以前的叫法,现在早改职中了。你沿前面这条路向南米左转朝东一拐就到了。” 就这样,她提着用塑料袋装的火晶柿子,敲开了我的门。 “我是xxx,常青介绍我来的。” 我当时很吃惊!不仅仅因为她突然到来,最主要是她竟然拿着我最爱吃的火晶柿子!我纳闷,难道常青给她讲的?不应该呀!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火晶柿子?”由于紧张我忘了礼节唐突地问。 “真不好意思,这是我在街上买来自己吃的,没吃完,想着你也许也喜欢吃,顺便带着来了。不太礼貌,别介意,我这个人就是不把自己当外人,还好你还真喜欢。”她难为情地说。 这样一来难为情的反倒是我了,我支吾着不好意思地说:“应该我说别介意,谢谢你拿的火晶柿子,请进吧!”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因为火晶柿子而陷入尴尬,但又因为爱吃火晶柿子拉近了距离,找到了打开冷场的话题。 很遗憾我们最后没有成。婚姻这种事原因很复杂,有些时候根本说不清楚。常言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也许就是缘分没有修到吧!但我们后来却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不满你说她的先生后来还是我和常青一手撮合的。现在夫妻恩爱,今年十一儿子结婚我也是跑前跑后,累得不亚于她夫妻俩。现在夫妻俩在家只等着抱孙子享天伦了。她的先生比我大两岁,我称他董哥,但要叫她嫂子,我却是一直叫不出口。她的儿子乳名叫红红,是不是和红红的火晶柿子有关,我想问但一直没开口。 在我和她处朋友的那段时间,一直至现在作普通朋友,只要去她家或者她来我家,赶上时令,餐桌上盛在洁白盘子里那红红的火晶柿子是绝不能少的一道水果。我们常一起一边拉着家常,一边剥掉柿子皮饱口福,然后我和董哥品着茶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电视,海阔天空地乱侃,等候着享用她和爱人在厨房各献厨艺倒腾的大餐。也不知道我和她游走于朋友边缘的情意,火红细嫩的柿瓤塞在嘴里面露喜色的董哥和我的爱人,吃没吃出别的味道,但她的那份心意我懂,我的那份用心我相信她也一定懂。 老同学高君 中学时的同学高君,在泉城济南上班多年,常自嘲自己差不多一半身子已是山东人。去年国庆回来了一次,正好赶上中秋,多年不见聚了一下,相邀去爬骊山追忆“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往昔。站在山顶上看到了满山成堆连片的红色夹杂着斑斑点点的墨绿和浅黄,像一片片红霞挂在山梁或坠入沟壑。 “那红色的是不是枫叶,我记得在这儿以前没有枫树啊?”高君不无兴奋地说。 我说:“那是柿子树,柿树叶经霜打之后就像枫叶一样红,当然柿子也是红的。” “这绝不逊色于北京香山的红叶!枫树的叶只能观赏,而柿子树则不同,不但叶子血红可以观赏,红红的柿子也是一景,还是味道很好的水果,尤其是咱临潼的火晶柿子,那简直就是临潼或者说西安一张美丽的名片。” “再晚些时候,进入深秋柿树叶全都凋落了,那满树缀着的柿子就像挂了一树树红红的灯笼,在蓝天白云下更好看!” 他深情地看着漫山遍野的柿子树,稍微停顿了一下说:“柿子在我国栽植面积很大,北方大部分甚至南方江浙一带都有柿子。这些地方我差不多都到过,也吃过那里的柿子,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最好吃的还是咱家乡的火晶柿子。以前我给同事和朋友讲,他们还老不服气,后来老父亲从家乡特意给他的孙子寄去一箱临潼正宗的火晶柿子,分给他们品尝后,全都面露喜悦一个个伸出大拇指。也就是从那时起多了一件负担,几乎每年柿子成熟的时候一定要托老家给朋友寄一些火晶柿子。” “你说的正宗火晶柿子是叔从哪儿弄的?” “听父亲说就是从我家附近的白鹿观一带。” “临潼的火晶柿子在全国最著名,但在临潼最好的极品火晶柿子应该是县东山任一带!” “不会吧,临潼就这么大地儿,还会有多大区别?” “当然啦!你若不信,咱们可以亲自去吃一下山任的柿子,一比较你就知道了。” 于是我们下了山,驱车来到了兵马俑南面的山任村。我挑了一个熟透了的火晶柿子,快速剥了皮递给他。高君只咬了一口,马上眼发异光脸露喜色,咀嚼着不住点头说确实不一样。最后本来说好只买一箱,结果买了好几箱后备箱差不多塞满了。在返回的路上,坐在副驾驶上的高君一脸兴奋,看着路边不时闪过的挂满果子的柿子树和石榴树,好半天说了一句话:“走遍天南地北其实在骨子里我永远是临潼人。就好比人的外貌可以改,甚至美容或者易容得面目全非,但基因和血统还有口味永远变不了!” 今年柿子熟了,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itongpizw.com/htpcd/10951.html
- 上一篇文章: 最全中药分类性味归经功效汇总上
- 下一篇文章: 双十二来了,这个你可别错过12月12日